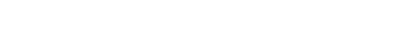信里的家国情怀
〇李剑锋
我的家乡在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交道镇北社村,在村西南有座陵园,园内有座纪念碑,那就是埋葬李育才烈士忠骨之地。我们两家同处一条巷道,炊烟相望不过百米,爷爷与他是同辈之人,儿时常听爷爷讲述李育才烈士和他的家书故事,那些穿越战火硝烟而来的故事与家书,如同一颗颗红色的种子,深植于我童年的心田,成为我最初且深刻的红色启蒙。
卢沟桥事变发生那年,李育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次年投身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。他在信中写道:眼下局势紊乱,此次抗战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,大家都肩负着民族解放的重任。那时日军已打到灵石,又退至娘子关外,他写“不少同学无家可归”时,笔墨里浸着泪水;写“淼源受伤”时,笔尖顿时生疼。最让我心惊的是那句“日军妄图灭我种族,儿绝不屈服”,当一个青年在信里写下“绝不屈服”,他不是在告别父母,那是在替整个民族立下誓言。他说“在外漂泊锻炼了筋骨”,年少的我只当是寻常家话,直到后来才懂得:那“筋骨”是用战火淬炼起来的担当。当他把“个人命运”与“国家存亡”写在同一张信纸上,那些横撇竖捺之间站着的是整个民族的脊梁。
在随后的战争中,李育才历任班长、连长、副营长等职务,转战于襄陵、汾阳、交城、太原等地。1941年12月被日军俘虏,送往东北做劳工,受尽折磨也没有变节,后多次越狱成功脱困,回到了部队。他在信中写道:那时给敌人做工,今天又继续为中华民族、为革命服务了。那时生活不自由,经常受气,现在呢?已完全进了自由幸福快乐的场所,回到了我所热爱的岗位。两种生活态度对比写出了家国情怀,写出了革命乐观主义。随后,笔锋一转,又柔成绕指的牵挂:儿很想念你们,想念家中及故乡之一切,但是民族革命尚未成功,敌人还占着我们许多土地,需要把他们赶出去,求得全国人民之自由,国家之独立。因此,还得继续努力,以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任务。抗战胜利后,在以后的解放战争中,他带领一个营遭敌三个团围堵壮烈牺牲,最终与父母没再见上一面。
每每听到这些文字,我总会看到两个李育才:一个在战场上冲锋陷阵,钢枪挑破夜色;一个在油灯下展纸提笔,笔尖落满对父母的愧疚。他写“民族革命尚未成功,需赶敌人出国土”时,分明是把“小家”的思念叠进了“大家”的蓝图里。这种“舍”与“不舍”的挣扎,恰是最动人的赤子心,他不是没有软肋,只是把对家国的大爱,当作了最坚硬的铠甲。那些关于“汽车、火车”的憧憬,不是一个普通爱国青年的乡愁,而是一个战士对国家未来的描摹,他把个人的归期,镌刻成了整个民族的春天画卷。
如今,我已过知天命之年,每每回村路过陵园,总觉得那些家书从未泛黄,故事还似在昨天。李育才家书里没有豪言壮语,却用最朴素的情感写出了中国人的家国信仰:是“国破时挺身而出”的勇,是“囚笼中不改其志”的韧,更是“愿以寸心换山河”的痴。正是无数这样的信笺,在战火里织成了民族的精神经纬。它让我明白,所谓家国情怀,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,而是有人把“我”活成了“我们”,把“小家”的灯火,种进了“大家”的星河。(山阳煤矿公司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