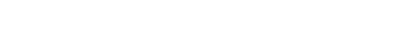镌刻在三秦大地上的初心
〇徐玉倩
西安城墙含光门的城砖上,深浅不一的弹痕像一只只凝视时空的眼睛。指尖抚过那些凹陷处,仿佛能触到1937年深秋的灼热——日军飞机俯冲时的轰鸣犹在耳畔,守城士兵的呐喊穿透岁月,砖缝里嵌着的半片弹壳,至今还沾着当年的硝烟味。这些伤痕没有随风雨褪色,反而在数载春秋里生长成城市的年轮,圈住了烽火岁月里的勇气,也圈住了和平年代的珍惜。
临潼华清池的五间厅,玻璃上的弹孔像一枚枚凝固的星火。1936年12月12日凌晨,枪声撕破骊山的寂静,张学良将军的卫队举枪时,枪托在青砖地上磕出的凹痕至今清晰。那扇被流弹击穿的玻璃窗,裂纹像极了当时中国的命运图谱——破碎却未断裂。在西安事变纪念馆,泛黄的《张杨对时局宣言》手稿上,“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”八个字被岁月浸得发褐,笔尖划过纸面的力度却依然能感觉:“我们不愿做亡国奴”的墨迹力透纸背,晕染出一个民族在危亡时刻的觉醒。
延安宝塔山的灯光,曾是暗夜里最亮的星。枣园的煤油灯盏里,灯芯结着的灯花仿佛仍在跳动,照亮过《论持久战》的手稿,也映过战士们补丁摞补丁的袖口。南泥湾的镢头静静躺在展柜里,木柄上的汗渍印子深浅交错,那是三五九旅将士们把荒山野岭犁成良田时,掌心与木柄较劲的痕迹。如今,延安革命纪念馆的雕塑前,常有孩子指着战士们紧绷的肩膀问:“他们累吗?”答案藏在雕塑底座渗出的草芽里。
铜川照金的薛家寨,悬崖石洞的崖壁上还留着红军战士刻下的箭头。1933年的寒夜,刘志丹带领游击队在石洞里煮过土豆,炭火把岩壁熏出的黑痕与刺刀刻的“为人民”三个字重叠。当地老人说,那时战士们揣着冻硬的窝头打仗,伤口发炎了就用草药敷,可唱起《红军纪律歌》时,声音能惊飞崖顶的鹰。照金纪念馆那支老式步枪的枪托上,“为人民”三个字被摩挲得发亮,像颗永不生锈的钉子,把初心钉在了黄土地上。
西安交大西迁博物馆里,1956年的绿皮火车模型前总围着孩子。玻璃展柜里,教授们当年用过的搪瓷缸沿磕出了豁口,里面仿佛还盛着从上海带来的海水——数千名交大人坐着闷罐火车西迁时,有人把家乡的海水装进瓶里,后来倒进了西安的井中。那些泛黄的教案上,公式旁边偶尔会出现“想念上海的雨”的小字,却又被“这里的星星很亮”的批注覆盖。如今,老教授们的实验记录本与年轻学子的芯片研发图纸并排陈列,纸页间的笔迹虽隔了半个多世纪,却都写着同样的执拗:要让黄土地长出科学的春天。
站在西安奥体中心的穹顶下,看夕阳为河水镀上金边,忽然懂得那些历史的细节为何如此鲜活。黄帝陵的古柏用年轮记录着沧桑,西安城墙的弹痕在春雨里抽出新绿,延安窑洞的窗棂映着新时代的灯火。那些长眠在烈士陵园的英魂,那些西迁路上留下的足迹,都化作了秦岭的草木——根扎在历史的沃土,叶向着未来的阳光。当风吹过奥体中心的钢构屋顶,发出的声响像极了冲锋号与建设者的哨声在时空里和鸣,告诉每一个行走在三秦大地上的人:英雄从未远去,他们只是化作了我们脚下的路,指引着我们走向更辽阔的远方。(煤机公司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