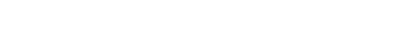红缨枪与肩章的对话
〇马明康
站在云周西村那方黄土高台上,风卷着麦浪掠过耳畔,恍惚间竟与军营的号角声重叠。眼前这尊汉白玉雕像,15岁的刘胡兰昂首挺胸,红领巾在风中猎猎作响,像极了队列里最挺拔的那抹橄榄绿。作为一名退伍军人,我曾在训练场上无数次挑战极限,却从未想过,七十多年前这片土地上,一个比我当年还小的姑娘,用怎样的勇气直面了真正的生死抉择。
铡刀前的正步
纪念馆玻璃柜里,那把锈迹斑斑的铡刀泛着冷光。讲解员说,当年反动派就是用它铡断了七根不屈的脊梁。我下意识挺直脊背——这个动作刻在骨子里,是军人对烈士的本能致敬。1947年那个寒冬,15岁的刘胡兰被押到这里时,是否也像这样挺直了腰杆?
档案里记载着她最后的对话。“说出党员名单,给你好前程。”敌人的威逼在她听来,或许就像战场上的虚张声势。“我是共产党员!”这声回答,比任何冲锋号都响亮。后来我在部队学战术课时才懂,真正的勇气从不是莽夫之勇,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决绝。就像我们在演习中明知“暴露”会被淘汰,却依然选择为战友掩护——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担当,原来早在七十多年前,就被一个少女写进了生命的终章。
展柜里那枚褪色的木质党徽,边缘被摩挲得光滑。讲解员说这是从她贴身衣物里找到的,或许在就义前,她曾最后一次抚摸过它。这让我想起新兵授衔那天,冰凉的肩章贴上肩头时,连长说的那句话:“从今天起,你的命就不再只属于自己。”
红缨枪与钢枪
在儿童团展区,一杆红缨枪静静倚在墙角,枪头的红绸早已褪色成浅粉。说明牌上写着:“刘胡兰曾用它站岗放哨,盘查可疑人员。”我忽然想起下连后第一班岗,握着冰冷的钢枪在雪里站了两小时,班长检查时却说:“站岗不是摆样子,是要真能挡住风浪。”
13岁的刘胡兰显然懂这个道理。档案记载,她曾在村口盘查时识破过伪装成货郎的特务。那特务腰间藏着短枪,却被她三言两语问得破绽百出。如今想来,这种警惕性与我们在边境巡逻时的状态何其相似——草叶的异常摆动,风中夹杂的陌生气息,都可能藏着不寻常。不同的是,我们身后有整个国家的力量,而她只有一根红缨枪和一颗赤诚的心。
展厅拐角处,一组蜡像还原了她纺线支前的场景。灯下的少女神情专注,手指在纺车上来回穿梭,线锭上的棉线渐渐饱满。这让我想起部队里的针线包,入伍时母亲塞给我的,说“自己的衣服自己补,别让人笑话。”后来在野外驻训,我用它缝补过磨破的作训服,也帮战友缝过松动的纽扣。原来穿过军装的人都懂,战场从不止于硝烟弥漫处,指尖的棉线与枪膛的子弹,同样是保家卫国的武器。
永不褪色的军礼
离馆前,我在留言簿上写下:“向战友刘胡兰致敬。”这个称呼或许有些冒昧,却出自肺腑。在部队时,我们常说,“牺牲是军人最高的荣誉。”但直到站在这里才真正明白,有些牺牲比胜利更能定义信仰。
返程路上,车过吕梁山脉,沟壑间的梯田如绿色的波浪。同行的老乡说,这些年村里搞红色旅游,年轻人都愿意回来创业。这让我想起退伍时的场景,教导员拍着我的肩说:“脱下军装也是兵,在哪儿都要站成标杆。”暮色中,纪念馆的灯光渐次亮起,照亮了“生的伟大,死的光荣”八个金字。我下意识抬手敬礼,这个动作里,有对前辈的仰望,有对军装的眷恋,更有对和平年代的警醒。或许正如那尊雕像所示,真正的英雄从不会老去,他们只是化作了星辰,照亮后来者前行的路。
而我们,无论是穿军装的还是已脱下军装的,都该记得:有些哨位必须有人站,有些担子必须有人挑,有些信仰必须用一生去守护——就像78年前,那个15岁的少女用生命告诉我们的那样。(董矿分公司)